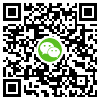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十一月下午,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案卷,窗外雨水顺着玻璃滑落,像在诉说着人间的无奈,电话突然响了,铃声刺耳得让我心头一紧。来电的是个陌生的男声,带着几分哽咽:“张律师,我是赵伟,我妈被我哥他们扔在养老院不管了,我想告他们要赡养费,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”赵伟的声音里满是愤怒和自责,我约他第二天见面,心里已经开始盘算,这会是一场关于赡养费的复杂纠纷,背后还藏着家族的冷漠和情感裂痕。
赵伟,42岁,走进办公室时,穿着一件旧夹克,手里攥着一叠养老院的缴费单和几张母亲的照片,眼神里透着疲惫。他母亲王阿姨,72岁,早年丧夫,一手拉扯大三个儿子。大儿子赵强、二儿子赵明都成家立业,收入不菲,却把王阿姨送到养老院后就鲜少露面。赵伟是小儿子,在外地打工,每月寄钱给母亲,可最近王阿姨生病住院,他们兄弟俩推来推去,谁都不肯出钱。赵伟气得发抖:“我妈为他们操劳一辈子,现在他们说‘没义务’,我咽不下这口气!”
我问他:“你有证据证明他们不尽赡养义务吗?比如聊天记录或养老院证词。”赵伟拿出手机,翻出一堆微信截图,大哥赵强在群里说:“妈有养老金,自己管自己。”二哥赵明直接拉黑了母亲。照片里,王阿姨躺在病床上,脸色苍白,身边只有赵伟陪着。我翻看了材料,证据扎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67条,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,不得因父母经济情况而免除。赵伟作为原告,可要求兄弟共同承担赡养费。
我告诉赵伟,这案子不简单,先要收集更多证据,证明王阿姨的生活需求和兄弟的经济能力。他点点头,眼神里多了几分决心。接下来的几周,他开始像侦探一样行动:他拍下母亲的医疗单据,住院费2万多,他一人垫付;他还找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,写下证词,证实赵强和赵明半年没来看过母亲。最关键的,是王阿姨的银行流水,显示她养老金每月只有3000元,不够医药开支,而赵强和赵明开的公司年收入超50万。
赵强他们却不甘示弱。他们找了个律师,辩称王阿姨有养老金,不需要额外赡养,还提交了一份所谓“协议”,说母亲早年同意“自食其力”。我一看就知道,这协议漏洞百出——没有正式签名,只有赵强的口头记录,不具法律效力。我建议赵伟申请法院调查兄弟的经济状况,同时请养老院工作人员出庭作证。
开庭那天,赵伟紧张得手都在抖,坐在原告席上,眼神却透着坚定。赵强的律师大谈“母亲自愿”,试图用旧协议压人。我当场提交了医疗单据、证词和银行流水,证明王阿姨生活困难,兄弟有能力却不履行义务。我问赵强:“你说母亲自食其力,可她住院时你为什么不出一分钱?”他支吾着答不上来。养老院工作人员出庭,激动地说:“王阿姨常哭,说儿子不来看她,只有小儿子赵伟每月寄钱!”
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,法官仔细核对了流水和医疗记录。最终,法院认定赵强和赵明违反赡养义务,判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500元,并补齐过去半年的住院费1万。散庭后,赵伟长舒一口气,对我说:“张律师,谢谢你,我妈终于能安心养病了。”可我看得出,他眼底的失落——这场官司赢了,兄弟间却再无情分。
走出法院,雨还在下,赵伟裹紧了夹克,背影有些孤单。法律保住了他的权益,可家族的温情,早已在赡养的争端里碎得一干二净。这场赡养费的博弈结束了,但赵家的心酸,怕是还要在母亲的病床上延续许久。